文/周重林、李明
為你留一座城,好喝茶
那個年代,在北京可以「打茶圍」,在上海可以「陪吃茶」,成都也有女茶房。男人可以在公共空間選擇更多的喝茶方式,女人的局限就多一些。而在公共空間和私人領地的自由切換,男人似乎也有改變主意的權力。豐子愷觀察下的舊上海茶生活,是一個特定區域。林語堂對北京類似區域也有觀察,「男士們也可以去她們的閨閣品嘗瓜果、飲茶閑談,坐上個把時辰離去,這叫『踏茶圍』,如此則男人一晚可去幾處談笑玩耍—— 風雨交加的夜晚或客人飲酒過量,他們也可以留下過夜,這叫做『借乾鋪』*」。我們的朋友胡適之更是深諳此道。
編按:借乾鋪,以前指借妓院住宿而不嫖妓。
概要之,我們很難以統計資料的方式具體印證公共空間和私人領地,哪一個對男女關係影響更大一些。但每一個時代的男女遇到的情感困境多少與這兩者息息相關。當公共空間的某些功能退化,男人們可靠的選擇就是回到家中,陪著妻子,哄著孩子,笑容滿面地接過妻子遞來的一杯熱茶。反之,如前文的佟振保般,即使娶了賢慧太太,一樣在外面花天酒地。
張愛玲遇到的問題,跟任何一個普通人遇到的問題沒什麼兩樣。她自己也明白,「去掉了一切的浮文,剩下的彷彿只有飲食男女這兩項。人類的文明努力要想跳出單純的獸性生活的圈子,幾千年來的努力竟是枉費精神麼? 事實是如此」。
一九四六年二月,張愛玲從上海去溫州尋找胡蘭成,迎接她的還有一個叫范秀美的女人。張愛玲本來喜歡在公寓裡喝茶,有一天終於明白,還有更廣闊的喝茶空間。這一次,她要為白流蘇留住那個陪她喝茶的男人。
吃完了飯,柳原舉起玻璃杯來將裡面剩下的茶一飲而盡,高高地擎著那玻璃杯,只管向裡看著。流蘇道:「有什麼可看的,也讓我看看。」柳原道:「你迎著亮瞧瞧,裡頭的景致使我想到馬來的森林。」杯裡的殘茶向一邊傾過來,綠色的茶葉黏在玻璃上,橫斜有致,迎著光,看上去像一棵翠生生的芭蕉。底下堆積著的茶葉,蟠結錯雜,就像沒膝的蔓草和蓬蒿。
二○○七年,同名電視劇《傾城之戀》完全照搬了這個喝茶場景,演員黃覺和陳數細膩逼真地呈現了小說中兩人間的互動對話。在書中,花花公子范柳原見到離了婚的白流蘇,一開口,就誇她的特長是低頭。這跟現在誇女孩長得漂亮是一樣的。細微差別在於,范柳原是此中老手,他在努力呈現差異性,以便誇得有新意。就像胡蘭成誇張愛玲是臨水照花人,從此成為江湖絕響。
在接風宴會上,范柳原突然出現,拉著流蘇跳舞,順便進行了關於好女人和壞女人的「學術交流」。范柳原認為,一般男人既喜歡把好女人變成壞女人,又喜歡拯救壞女人。他則不同,喜歡老實些的好女人。白流蘇將這個說法解讀為,范柳原理想中的女人是人前貞女,人後蕩婦,冰清玉潔又富有挑逗性。她也很會來事,順嘴還了范柳原一句:你要我在旁人面前做好女人,在你面前做壞女人。逼得范柳原將他對流蘇的審美提高到「一個真正的中國女人」的境界,他的立論依據是:這樣的中國女人最美,永不過時。
不等舞會結束,范柳原找了個藉口,製造了兩人獨處的機會。在一堵牆前,兩人又討論起了地老天荒的問題。白流蘇還忖度范柳原是講究精神戀愛還是肉體之愛。因為范柳原覺得,精神戀愛是以結婚為導向的,而結婚後,女人在處理具體家務上有很大的主導權。白流蘇傾向於認為范柳原是講究精神戀愛的,到底也拿不準,所以兩人在飯店吃完飯後,藉著這次喝茶,又來了一次交鋒。
范柳原說茶葉景致讓他想起馬來的森林,白流蘇卻覺得堆積的茶葉像蔓草和蓬蒿。范柳原的說法伏了後招,他說要陪流蘇去馬來,回歸自然。范柳原假設了馬來場景,也在試探白流蘇,並將流蘇穿旗袍更好看作為審美品味又攻了一招。結果,兩人共同討論了人前裝腔的有效性,當然也得有人說真心話。范柳原還說,自從在上海第一次見流蘇之後,他就上了心,還為她費了不少心機。
胡蘭成在武漢,張愛玲不在身邊,同樣費了心機,他提前享受了「紅袖添香」的情趣,俘獲了一個周姓小護士,要了人家的照片,並讓人家題字,周題寫的內容是「春江水沉沉,上有雙竹林,竹葉壞水色,郎亦壞人心」。原本,這首樂府詩是胡蘭成教她的。
范柳原說了那麼多話,如果白流蘇還不接招,那就玩不下去了。從此,兩人一起做了很多事情,看電影、上賭場、去綢緞莊,范柳原卻突然成了君子,連她的手都難得碰一碰,唯獨在沙灘上來了一次驚喜,兩人互相拍打對方身上的蚊子,玩得很開心。沒想到,流蘇突然不爽,起身就走。按一般男人的邏輯,范柳原應該追上去哄流蘇的,但他卻很淡定,轉身摟個妹子曬夕陽去了。胡蘭成在鄉下逃難時,順手也搞定了寡婦范秀美。
從此,范柳原整天和那個白流蘇認識的妹子廝混,直至與白流蘇討論吃醋問題時,才和解。白流蘇也疑心范柳原使的是激將法,在逼她主動投懷送抱,卻也留了後招,如果出事,可以正大光明地推脫責任,事了拂衣去,再找其他女人。於是,兩人又貌合神離,范柳原解釋《詩經》,說是人力有時而竭,流蘇說,你繞個大彎子,就是不想結婚。一番爭執之後,流蘇回了上海,面對事關清白的輿論壓力,她選擇了靜坐等待,直到後來范柳原來電報求她去香港。范柳原去接她,打趣她的綠色玻璃雨衣像「藥瓶」,冷不防又來一句:「你就是醫我的藥。」
上海往事,茶裡人生
出生在上海,在香港求學多年的張愛玲,要借助這個處於特殊時期的城市表達她對上海的懷念。李歐梵解釋說:「在我看來,香港大眾文化景觀中的『老上海風尚』並不光折射著香港的懷舊或她困擾於自身的身分,倒更是因為上海昔日的繁華象徵著某種真正的神秘,它不能被歷史和革命的官方大敘事所闡釋。這就是他們所希望解開的神秘,從而在這兩個城市之間建立起某種超越歷史的象徵性聯繫。這在近年來製作的幾部引人注目的關於上海的電影中尤為明顯:徐克的《上海之夜》,關錦鵬的《阮玲玉》和改編自張愛玲小說的《紅玫瑰與白玫瑰》。」
喝茶是上海風尚的一個組成部分,關錦鵬們勾連「上海往事」(二○○七年上映,講述張愛玲傳奇一生的電視劇也叫《上海往事》),不得不從張愛玲那裡尋找認同,因為他們曾經被歷史切割過。至於用什麼方式去呈現,是小說,還是電影,都無法改變上海生活的本色。二○一三年,厚積薄發的金宇澄在《繁花》中,讓陶陶招呼滬生吃茶,也是開講「上海往事」,從一件事講到另一件事,縈縈繞繞,牽出許多人,許多事。他們出遊,吃飯,常去喝茶的地方,有「綠雲」茶坊、「香芯」茶館。
一次,梅瑞和康總一邊喝茶,一邊聊天,梅瑞雖然講到與陶陶、滬生談過戀愛,跟現任老公結了婚,生了孩子,卻力證自己是一張白紙,不懂男女風情。但在康總眼裡,梅瑞「待人接物,表面矜重,其實弄風惹雨,媚體藏風」,自然不是省油的燈。又一次,梅瑞聊起她媽想跟她爸離婚,跟一個舞伴結婚,她媽說:「這叫第二春,等於一季開兩次桃花。」康總說:「等於一年採兩次明前茶*。」
編按:明前茶,清明節前採製的茶葉,少蟲害、質佳量稀,較昂貴。
陶陶跟老婆芳妹離了婚,以為即將要娶的小琴愛自己,誰知兩人調情嬉鬧中,小琴從陽臺上摔下來,死了。後來陶陶找到她寫的一個日記本,才知自己不過是便宜的下家。電視劇《紅蜘蛛》中有一個類似情節,講的是一個漂亮性感的失足女青年嫁了一個老實巴交的男人。有一天,男人看到女人寫的日記,才知一切因果,那份日記寫得極詳細。《繁花》中的兩個男主角,阿寶和滬生,一個一直不結婚,一個一直不離婚。
所有故事的底色,或如《繁花》結尾的一段話:「面對這個社會,大家只能笑一笑,不會有奇蹟了。女人想搞懂男人的心思,瞭解男人的內心活動,請到書店裡,多翻幾本文藝小說,男人的心思,男人的心理活動,裡面寫了不少,看一看,全部就懂了。」
因為,這本就是生活的底色,多喝雞湯無用,八卦星座也是枉然。茶館裡的普通男女,能夠說出來的,終究是陳詞濫調,而想說的,不能說,不可說,不便說,這才是人心的隱秘。有心勾引,認真失身,情中有景,蜜裡調油,很多時候,也許是惡夢。《繁花》裡,芳妹總結說:「老實女人是重磅炸彈,炸起來房頂穿洞。」
在《傾城之戀》中,一番波折之後,藉著戰亂,張愛玲成功為白流蘇留下了范柳原。私心裡,她也想留住胡蘭成,終究沒有成功。一九四七年六月,張寫信與胡了斷關係,隨信附有三十萬元。晚年,張愛玲生活在國外,另嫁他人,喝茶的日子漸少,喝咖啡的日子漸多。她深居簡出,又過上了公寓生活。於她而言,享受燦爛和承受孤獨,彷彿是宿命般早已註定。在這點上,她和弘一法師看起來很相似。張愛玲卻說:「不要認為我是個高傲的人,我從來不是的,至少,在弘一法師寺院轉圍牆外面,我是如此的謙卑。」
如果往回追溯,那一年,張愛玲的外曾祖父李鴻章參加李叔同父親李筱樓的葬禮,對年幼的李叔同勉勵有加。在李鴻章時代,李鴻章已經做得不能再好了。在李叔同時代,李叔同終於有主動的生命追求。而張愛玲,終於被滾滾紅塵所裹挾,時代和命運給她沖泡的那杯苦茶,她只能選擇喝下。一九九五年,張愛玲在美國寓所去世,骨灰撒入太平洋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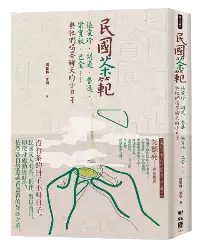 想了解更多民國才子佳人們對茶的嗜好與依賴,歡迎到《民國茶範:張愛玲、胡適、魯迅、梁實秋、巴金……與他們喝茶聊天的小日子》探索更多內容!
想了解更多民國才子佳人們對茶的嗜好與依賴,歡迎到《民國茶範:張愛玲、胡適、魯迅、梁實秋、巴金……與他們喝茶聊天的小日子》探索更多內容!(本文內容摘自《民國茶範:張愛玲、胡適、魯迅、梁實秋、巴金……與他們喝茶聊天的小日子》,由 聯經出版公司 授權轉載,並修訂標題。首圖來源:Laura Loveday flickr,CC Licensed。)





